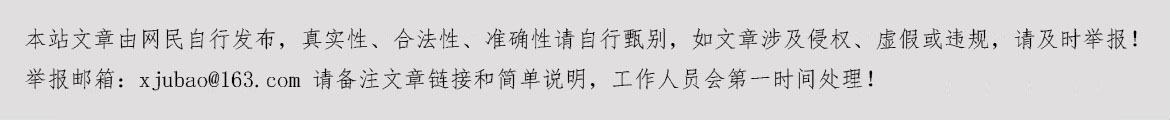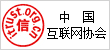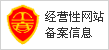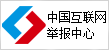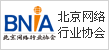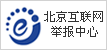早请他出山,李诞也不至于被骂
2023-03-22 13:05:27
盼望着,盼望着。
《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上终于来了一个作家,刘震云。
刘震云讲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开场秀。
没多少包袱,也不夹杂爆梗,通篇都是宛如小说一般的描写,充满了画面感。
果然,作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
今年越来越能感觉到,作家或许才是最适合上综艺的人。
《向往的生活》就两次验证这个真理。
前有许知远全程“打野”,带观众领略了海南风光。
后有刘震云去做客,不仅毫无作家的严肃做派,反倒是演绎了什么叫“三句话,我让黄磊为我加了三个菜”。
这两位文化人,让索然无味的综艺变得生动起来。
作家上综艺,比我们预想中,要有趣得多。
在了解到作家的真实性格之前,我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肯定是严肃的、沉稳的,讲起话来总是端着的。
万万没想到,这群人的真实性格自带反差萌。
有的是老顽童,有的冷幽默大师,出口就是笑话。
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余华。
也是她姐最希望能在综艺里看到的作家。
余华,一个神奇的人。
上学的时候,读余华的书是一种风潮。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
那时候,读的是苦难,是飘摇的人生,是残忍的命运。
然而到了今天,余华却成为了我的互联网精神药片。
每当心情低落,就去看几则余华笑话。
药到病除。
把快乐留给自己,把痛苦留给读者
对于余华其人的幻想,很多人都曾有一个天大的误会。
那就是,写苦难的故事,必定是个苦大仇深之人。
他的笔下,人如蝼蚁命如草芥,只是目睹每个角色的境遇,都让人感叹作者的狠心。
然而余华本人,只要看过采访,无人不会惊叹于他的幽默。
余华谈努力写书,是为了过上一种不被闹钟吵醒的生活。
哪个社畜能不共情?
著名作家尚且如此,我们贪恋一点懒觉,何罪之有啊。
他谈躺平,也完全没有端起过来人的架子,教育当代人的懒惰。
恰恰相反,想躺平有什么错?
奋斗的最终目标,不就是为了躺平吗?
他谈精神内耗,也未必是消极的。
虽然人人都烦恼于自己的精神内耗,但换个角度看,“精神内耗是在寻找一种出口”。
如果什么都不耗,那连寻找出口的动力都没有了。
所以有内耗,也可以是积极的情绪啊。
这些风靡互联网的热词到余华嘴里,全然没了之前的沉重。
三言两语,就犹如四两拨千斤,听完只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余华和苦大仇深,距离可太远了。
他更像是个从事喜剧创作的人,热爱插科打诨,一句话不加梗就难受。
别人问他,给自己作品打几分。
他说豆瓣是9.4,他也打9.4。
“剩下的0.6去问问豆瓣。”
别人问他,现在拿版税能赚多少钱。
他不正面回答,只是表示:
“我靠《活着》活着。”
别人评价他还以为是个苦大仇深的中年人,他倒为了“中年人”三个字高兴起来。
因为成名太早,许多人都以为余华已经年事已高,更有甚者还以为他已经作古了。
“天呐,他还在啊,我以为他不在了。”
其实余华是1960年生人,今年也才62岁。
很难想象,书中那些残酷的际遇,居然出自一个总是乐乐呵呵的老顽童之手。
这反差不亚于画遍世间美好的宫崎骏,和创造惊悚无数的伊藤润二。
网友点评余华的句子最是贴切。
「把快乐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读者。」
而现在,这位把快乐留给自己的老顽童,也把快乐的余波带给了读者。
余华和罗翔有一个对谈节目。
一个作家,一个法律人,不同维度的思想碰撞非常精彩。
但让我惊讶的是,每当画面切到余华,弹幕就冒出来许多为他配的“画外音”——
余华老师:我不能再当搞笑男了
余华:我到底应不应该搞笑啊他好认真
余老师:这是免费的,我要认真听
这些弹幕搭配余华略显正经的神色,瞬间让对谈弥漫着一种轻松诙谐的氛围。
就连那些苦大仇深的书中,都能挑选出来各种金句,作为互联网的热转语录。
比如书中说:
「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我突然发现了逃跑的意义,它使惩罚变得遥远,同时又延伸了快乐。」
无论前因后果如何,单单一两句,总能恰到好处地适配到当下的心情。
当代人,真的太需要嘴替了。
“我们全家已经没有阑尾了”
余华笑话,还集中分布在他回忆童年的片段里。
大概作家都有这样的超能力,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生动的过往。
余华口中的童年便是如此。
「我写作就是回家。」
虽然生活在北京已经三十余年,但只要拿起笔,余华就会穿越回那个南方小镇。
他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在他的记忆中,那里有漫无边际的稻田。
小时候调皮总闯祸,余华为了逃过父亲的打,就会躲在稻田里。
父亲过来找的时候,余华就会装哭,用哭声给父亲一个信号,让他分辨出自己躲在哪。
有时父亲忙工作,他就躲在稻田里,一直躲到睡着。
为了逃课,余华还会在父亲面前装病。
一开始是装发烧,后来发现父亲会识破,便开始装胸口疼。
然而这一装病则已,父亲直接误以为他得了阑尾炎,带他上手术台割掉了阑尾。
余华回想起来,不无伤感地说:“我父亲的阑尾也割掉了,母亲的也割了,哥哥的也割了。”
“我们家已经没有阑尾了。”
父母都是医生,余华童年最熟悉的地方,除了稻田,就是医院。
那时,余华每天晚上都会被医院里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
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他的笔下经常谈及死亡。
余华还喜欢去太平间里睡午觉。
长大后他读到海涅的诗里写:“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他想起那时在太平间里睡觉的自己,正是这样的感受。
贾樟柯有一部以作家为主角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片名便出自余华之口。
在影片中,余华站在海盐县的海边,回想起小时候看课本里说,大海是蓝色的。
但家乡的海边,总是一片黄色。
他便想一直游,游到海水变蓝。
长大后,余华做了牙医。
那时的牙医不比今天,更像是一门手艺。
他第一天到了诊所,师傅跟他说,“你看一遍,下一个就你来”。
于是余华第一天就开始拔牙,拔了整整五年。
他算了算,从业以来,自己拔牙拔了有一万颗之多。
但余华厌倦极了。
他认为人的口腔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他决定转行,去文化馆。
开局确实很轻松。
他从《人民文学》看起,学别人如何写作,从标点符号的用法开始学起。
“什么时候应该是引号,什么时候应该是逗号,看了两页,行了,写吧!”
他自嘲认识的字不多。
评论家常称赞他语言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看完《如何写作》的宝典,他很快便开始创作。那时没有电脑,所有的稿子都需要手写。
天冷的时候,常常是写字的右手发烫,左手却冰凉。
“一个是活人的手,一个是死人的手。”
写完便寄到各大杂志,那时寄稿子的范围之广,比他现在去过的地方还多。
开局轻松,却不顺利,余华时常收到退稿。
来送退稿的邮递员,常常是把退稿一扔,甩进余华家的院子里。
退稿多到后来父亲一听院子里“啪嗒”一声,便知道,又有退稿来了。
但余华没停,一直退便一直写,最终真的凭着写小说,把自己成功转到了文化馆。
那时的余华,就颇有几分反骨和喜剧人天赋了——
第一天上班,他特意迟到了两个小时。
结果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的。
余华就知道,这个单位他来对了。
作家笑话,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1988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开学了。
余华遇到了自己的舍友,也是未来同行的伙伴,莫言。
一起在研究生院进修的那两年,余华和莫言每天在宿舍并排写稿。
有时写着写着两人抬头一对视,立马破功,灵感全无。
后来莫言在两人中间挂了一个旧日历,这才把书写完。
后来余华回忆起那时的生活:
“我曾和莫言在一个宿舍住了两年。我看书永远是躺着看,莫言当兵出身,读任何书都是坐在椅子上,姿态很认真。”
不过现在,余华说自己把坏习惯改掉了——
现在连写东西也是躺着的。
这群作家凑在一起,虽然写的都是《活着》《丰乳肥臀》《1942》等严肃文学,但实际上生活中却是个顶个的耿直幽默,致力于制造作家笑话。
如果非要起一个名字,我愿统称为,“口胡作家”。
即,胡话张口就来的作家。
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余华一行作家早年间受邀去国外,要演讲说一说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
他们立马开动自己的口胡超能力。
余华说是为了不做牙医,想睡懒觉;
莫言说是为了买皮鞋装军官;
王朔也胡诌了一个离谱的理由。
轮到苏童的时候,只有他准备的稿子是正儿八经的,羞得不愿上台。
刘震云也有这样的口胡经历。
有次他和余华一起出席活动,被人错认成余华:“余老师,您那本《活着》写得真好”。
刘震云张口就编了一段:“谢谢,那是我早期的作品。
你也可以看看《一句顶一万句》,看看《我不是潘金莲》,看看《一日三秋》”。
因为余华提前走了,他还好人做到底,帮余华在书上签了名。
但镜头对准签名的地方发现,刘震云大手一挥写下了八个大字:
“刘震云代余华签名。”
莫言看着稳重,其实也是冷幽默达人。
之前接受人物采访,记者问他:“您现在最希望的一种状态是什么?”
他咧嘴回答到:“我们结束采访。”
还有一次莫言被粉丝深情表白,“莫言老师,我要朗读一首你的诗歌献给你。”
莫言回忆说:“她朗读得声情并茂,目光里边含着泪光,我听了也很感动。
后来她读完了,我就说,如果是我写的该有多好。”
在这些作家笑话中,我最喜欢的是关于史铁生的故事。
有一阵子,辽宁文学院在搞足球比赛,余华、莫言、刘震云、马原就想带着史铁生一起去。
他们扛着史铁生的轮椅一路从北京赶到沈阳。
到了赛场上,他们特意为史铁生安排了守门员的位置,还跟对面的球员说:“你们一脚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
这招一出,对面的球员谁也不敢往史铁生那边踢了。
这怕是年份最早的地狱笑话了,当史铁生的父母还小心翼翼不敢触碰这个话题时,这帮损友直接跨了过去。
所以关于余华的点评还有一个翻版:
把快乐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读者,把球门留给铁生。
前段时间在《脱口秀大会》上看到庞博讲的一个段子,让我颇有感触。
他说现在短视频几分钟就可以让你看完《红楼梦》。
任何晦涩难懂的书放到短视频里,都可以变成小美和小帅的故事。
自己也已经好久没有正经看过书了。
其实,谁不是这样呢?
这好像是我们的时代病。
比起打开一部晦涩的好书,还是刷刷短视频更开心。
我们似乎变得越来越浮躁了。
回想起自己上学时候,还能认真读读余华莫言,然后三五好友交流读后感。
现在只愿意看看余华莫言的段子,然后转发给好友一起哈哈哈。
看书要看轻松的,追剧要追甜宠的,电影要选爆米花的。
别说读《活着》,光是预想一下要在书中和福贵一起沉浸式经历苦难,都不忍翻开。
对此,心理学家崔庆龙老师提出过「心理效能」这个概念——
我们越来越倾向于速食流量,是因为高质量的娱乐,需要充足的心理效能去支撑运行的。
很多时候我们青睐碎片化的事情,是因为仅有的心理效能水平无法负载大型程序。
当在一个人处于低心理效能时,是没有“余额”去启动娱乐这个行为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书,看电影,打游戏,一旦预期的反馈没有产生就会立刻关掉,或者频繁更换目标,这反映的是人们所剩的心理余额仅够支付“预览”,而不是投入。
这就是所谓速食流量能够崛起的原因,因为它充分“照顾”了人们普遍心理效能不足时能够获得的反馈体验,代价就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维持在这个行动水平。
现在连娱乐,都有了成本高低之分。
这当然有碎片化信息时代的弊病。
但也有一部分内耗,是源于我们对当下处境的无力感。
相比一部大部头带来的情绪起伏,还是简单的快乐更让人感到安全。
这些作家的故事,轻巧、搞笑,透着一股没心没肺的快乐。
反倒成了生活最好的消解。
她姐有时候也会忍不住陷入自己刷短视频、追无脑剧又浪费了一天的自责情绪里。
但有时候又转念一想,也罢。
心情低落,就不要苛责自己了。
给自己放一个小假,去看看作家笑话吧。
如果这些笑话还不管用,那就看看这只酷似余华的小狗吧。
毕竟,没有什么能比身心健康更重要了。
最后,点个「在看」,希望今天这篇文章,能给你带来5分钟的快乐。她刊